与零食的爱恨情仇
我又双叒叕吃上零食了,今天是草莓味加抹茶的快乐。
我,一个钱包总比肚子先叫的成年人,这辈子打过最持久的战争,就是和零食。一周吃N次,循环往复,却从不觉得腻。
我爱零食,爱得有点没出息。压力大了,一口甜,好像日子就没那么苦;无聊了,一包脆,咔嚓声比任何音乐都解闷。它像安插在平淡日常里的快乐内应,总在关键时刻策反我。
但我有个死对头,叫理性。每次手伸向货架,它就在脑海里开批判大会:“省下这钱,够你坐公交去面试!”“都多大了,还像小孩一样馋嘴!”道理都对,可越听越想叛逆。
于是我开始拖。今天想买?忍到明天。明天还想?那后天再说。结果越拖,那包零食在心里越发金光闪闪,从普通膨化食品直接升格为“童年梦想补偿礼包”。脑子里两个小人吵得不可开交:
理性说:“想想未来!”
感性喊:“未来太远,现在就要!”
最后,总是感性一脚踹飞了理性。
吃的时候是真快乐,像打赢一场胜仗。吃完也是真空虚,捏着空袋子,仿佛刚把银子亲手扔进风里。
这场战争,我屡战屡败,屡败屡战。
长久以来,我总觉得吃零食是件幼稚的事——就像父母总挂在嘴边的嫌弃。可舅舅一家却不一样。他总爱和表姐表哥围在桌边,尝着零食说“这个好吃”;舅妈会带他们去超市,大方地说“想吃什么就拿”。
我的童年没有这些。那时家里紧,三餐能饱足已。在学校,我看着别人吃辣条、舔冰棍,羡慕像藤蔓悄悄缠住心脏。我也曾鼓起勇气,跟母亲说:我想吃这个。可回应我的,永远是那句:“零食不好,吃了就不吃饭了。”
我也有过磨破嘴皮终于换来一包零食的时刻,但那短暂的快乐,却总在生病时变成母亲说教的引子:“让你吃!现在身体差了吧?”“都是垃圾食品害的,看病还要花钱!”
那些话,像细小的针,扎得人发不出声。在母亲的眼里,我的表现永远和她的认定不一样:我明明好好吃饭了,零食也不是天天都有。可她认定了的因果,便成了我无法反驳的“真相”。
有一阵,我帮同学抄作业换零钱,也偷拿过家里的钱去买零食。我知道不对,但欲望像滚石,拖得越久,坠落越狠。那时不懂为什么,后来才明白:我想吃的从来不只是零食,而是那种被允许的、名正言顺的甜。是像舅舅一家那样,零食摆在桌上,爱也摆在桌上;是像舅妈那样,伸手递来的不只是一包饼干,更是一份“你可以”的温柔。
我多希望,父亲也能坐在我身边,尝一口我爱的味道,说“这个不错”;母亲也能牵着我的手走过货架,告诉我“喜欢就拿”。
后来住校,有了生活费,能自由支配了,反而不怎么吃零食了。钱竟能省下不少。那时我不懂为什么,如今才明白:当“被禁止”的枷锁消失后,欲望反而变得轻了。
长大之后,我依然喜欢吃零食。更准确地说,我喜欢在父母面前吃零食。
有钱的时候,我会刻意买很多,散落在家里显眼的地方。没钱的时候,就忍着不吃,也绝不再开口说“我想吃那个”。
但我依然执着地,试图复刻舅舅家的那种氛围。我会买来快餐,要求母亲“陪我一起吃”。我们坐在桌边,咀嚼着那些曾被定义为“不健康”的食物。那一刻,空气里有一种笨拙的、被临时搭建起来的温馨。
我像是在进行一场沉默的展演。你看,零食无害,它甚至可以成为团聚的背景音。你看,我能负担自己的欲望了,甚至能“请”你们吃。
这或许是一种迟来的、孩子气的弥补。我不再索要,而是试图给予;不再争论对错,而是直接呈现结果。我想用此刻桌上具体的食物,去覆盖记忆里那些抽象的匮乏;想用一次并肩而坐的咀嚼,去兑换一点点童年时求而不得的、名正言顺的甜。
零食很轻,装在心事里却很重。我吃的或许从来不是那一口酥脆,而是那年那日,那个从未被满足过的、小小的自己。
这场与零食的战争,打到后来,对手早已不是理性,也不是父母。而是在与那个曾经眼巴巴望着货架的小小的自己,进行一场漫长的和解。
如今我一口一口吃下去的,是现在的自由,也是在对过去的自己轻声说:
“你看,我们终于可以,大大方方地吃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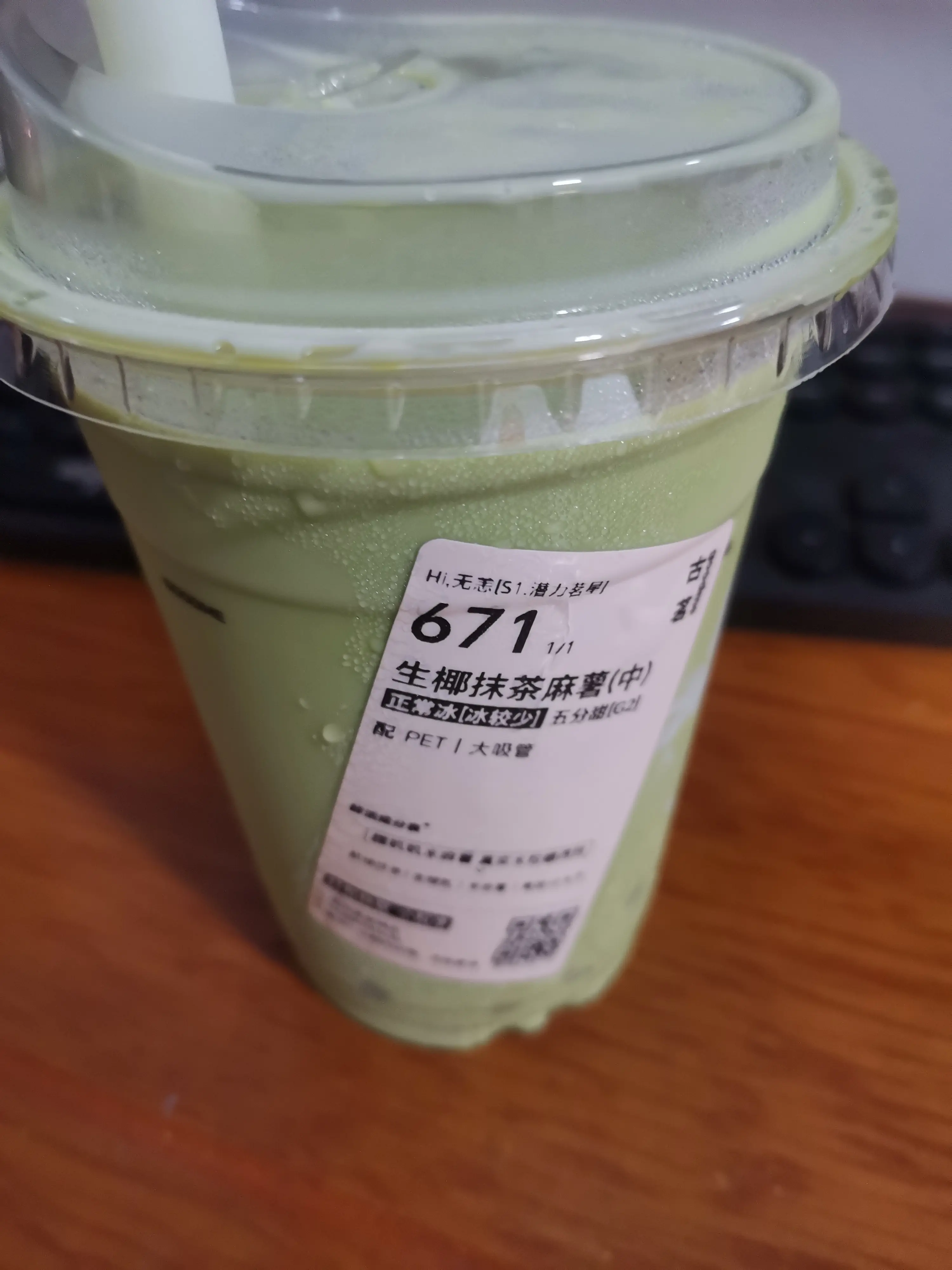


很喜欢喝香飘飘,因为母亲也喝过。如今,我动不动就捧一杯在手里。当身边的人都首选咖啡时,只有我握着一抹熟悉的暖甜,像是把某个安静的午后、一段未被说破的理解,都融在这小小的杯中了。


吃喜欢的零食,心情还是很愉悦的
喜欢的零食花样繁多 可惜每次吃过之后轻轻一呵 就像把白花花的银子散进了空气里 心情顿时就不美丽了
小时候也想吃零食,但是那个时候家里面都不太富裕,就等着春节才能有糖果吃。
现在还是喜欢吃蜜三刀,但是胃口不行,吃不了太多…
都不知道还有这东西的存在 小时候过年家里也没有零嘴 直到快上初中那会儿家境才真正宽裕起来 第一次去零食铺时 满眼都是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儿 每一样都对我充满了诱惑
讲道理还是以前小时候太缺了,现在有条件了就报复性消费。
没办法 报复性消费是自愈的一种 不痊愈就会出现盲目的给予 看不见爱人需要 一度以为自己缺的就是爱人的需求
童年报复性补偿,成年后养的第一个小孩,是小时候的自己。年少不得之物,终将困其一生。
网上很火的那句:笑着给我花钱的人 我终于找到了 就是我自己 爱你老己 明天见 有些遗憾大概就是这样 不是用来纠结的 是提醒我们好好爱现在的自己